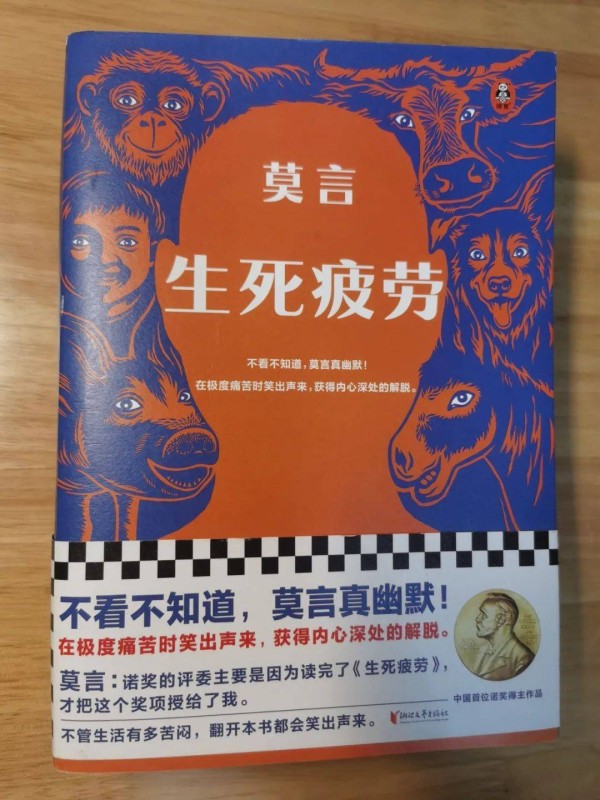王顺天:为何作家喜欢怀旧|中原作家
自制柔顺剂:使用等量的白醋和水,混合后加入几滴你喜欢的精油,可作为天然柔顺剂。 #生活技巧# #家居清洁技巧# #衣物柔顺剂配方#
作者:王顺天
来源:文艺报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琳蛋糕的滋味如魔法般打开记忆的甬道,这种通过感官触发记忆的机制,在文学创作里演变成了复杂的时间叙事技巧。汪曾祺在《受戒》里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此句告白揭示出文学创作中记忆与想象相互依存。作家提笔时,现实时间缩成记忆微粒,文学就在这些微粒间隙构建虚构之境。文学与怀旧的关联,体现在文本的方方面面。当汪曾祺描写高邮的鸭蛋,孩子们纽扣上挂着的“鸭蛋络子”,封存着故乡的晨雾、水乡的桨声和母亲的围裙。《受戒》里,记忆中荸荠庵的僧人生活、小英子的形象、庵前的荸荠地,经四十年沉淀,在文字里有了超越现实的澄澈质感。在沈从文的《边城》里,茶峒的渡船永远停泊在翠翠的等待中;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后花园的蝴蝶凝固在祖父的草帽上。作家们用文字的琥珀将流动的时间封存,创造出既属于个人又通向永恒的审美时空。
为何作家喜欢怀旧?从创作角度看,怀旧为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叙事维度和艺术魅力。首先,怀旧赋予作家在文本层面施展技巧的空间。通过回忆这一叙事视角,作家得以突破现实时间的限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中构建复杂的叙事网络。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借助回忆打乱时间顺序,构建起复杂而精妙的叙事结构,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流动的时间长河之中。其次,怀旧有助于处理个人情感与经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经历各种喜怒哀乐,而文学成为了他们抒发情感、铭记经历的重要方式。当现代性浪潮来袭,文学怀旧有了新意义。汪曾祺笔下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这不仅是味觉记忆重现,更是对抗文化同质化的象征。本雅明感叹“灵光”消逝,而文学怀旧叙事创造新“灵光”,如王安忆重构老上海弄堂、白先勇复现旧时月色,是对消逝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现代灵魂提供栖息之所。
文学意义上的怀旧,应定义在文本层面,也就是技巧、技法的层面。如果仅按照题材,将写过去生活的都视为怀旧,可能会过于泛化。一些描写过去生活的作品,若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事件,没有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情感表达手法,就不能简单地归为怀旧文学。而那些怀旧的经典作品,它们通过独特的文本技巧,如象征、隐喻、意识流等,将过去的生活片段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其具有了怀旧的特质。此外,文学的怀旧不仅关乎甜蜜的追忆,更包含着对创伤的救赎与超越。余华的《活着》中,福贵对往事的讲述本身构成生存的勇气,那些被反复咀嚼的苦难记忆,在文学的重构中获得了形而上的救赎意义。普鲁斯特在哮喘发作的暗夜里,用记忆的丝线编织出跨越世纪的宏伟画卷,病榻反而成为穿越时间的方舟。这种创伤书写的智慧,在东西方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形态: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描绘的“呼愁”,是整座城市对帝国斜阳的集体忧郁;而李清照“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慨叹,则是将个人遭际升华为对时间本质的东方哲思。汪曾祺在《虐猫》中处理文革记忆时,用孩童视角消解历史暴力的沉重,这种举重若轻的笔法,恰是文学怀旧的深层智慧——不是遗忘,而是将创伤转化为审美的结晶。这种创作行为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治疗功能。作家通过怀旧叙事完成对破碎自我的重构,在文字的炼金术中将个人创伤升华为集体记忆的丰碑。
现代语言学显示,“怀旧”的词源暗示了文学怀旧的困境——还乡难以实现。作家通过叙事策略创造“时间褶皱”:在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中,少年视角将历史暴力转化为成长寓言;余华《活着》以重复性叙事消解线性时间的暴政;而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则通过萨满教的环形时间观重构了现代性创伤。这种时间美学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共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形成镜像对话,两者皆以魔幻叙事抵抗历史的单线进化论。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文学的怀旧正是选择某个特定的分岔,将其固化为永恒的此刻。正如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所说的那样,“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河水依然倒映着四十年前的月光,普鲁斯特的玛德琳滋味仍在无数读者的唇齿间苏醒。当现代人困在即时性的牢笼中,文学的怀旧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永恒的窗。那些泛黄的书页里封存的不只是旧日时光,更是人类对抗遗忘的精神图谱。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记忆的守夜人,每部作品都是穿越时空的方舟。沈从文在《长河》中保存的辰河船歌,恰如敦煌卷子里的民间曲辞,在千年后依然跃动着生命的韵律;曹雪芹在大观园废墟上重建的青春王国,使那些凋零的海棠在文字中获得永生。这种记忆的永恒性,在数码时代获得了新的载体与形态。网络文学中的“无限流”叙事,通过主人公在不同时空的穿梭,实际上在解构线性时间的同时,重构了怀旧的多元维度。《三体》中云天明讲述的童话,既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密码,也是将个体记忆升华为文明记忆的壮丽寓言。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文学,会发现怀旧叙事正在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体系。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学回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激荡着新的涟漪。这些创作实践证明,文学的怀旧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过去,记忆不是过去的囚徒,而是未来的信使。
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回望,文学的怀旧更显其独特价值。当算法可以精准预测读者的情感偏好,当DeepSeek能瞬间生成怀旧文本,真正的文学记忆反而愈发珍贵——因为它承载着算法无法复制的生命温度。那些手写书信的墨迹,故纸堆里的批注,乃至汪曾祺笔下咸鸭蛋红油的质感,都在提醒我们:文学怀旧的本质,是对抗异化的精神操练。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在文字中所追忆的“逝水年华”,实则是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抵抗时间暴政的巴别塔。每个怀旧的文字都是塔身的砖石,而作家的深情就是最坚韧的黏合剂。这些散落在时空中的文学时刻,经由文字的神秘引力汇聚成璀璨的星河。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惘,终将在文学的永恒中觅得安放之所,因为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写,忽必烈让马可波罗为他讲讲威尼斯,马可波罗回答道:“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文学的怀旧叙事,正是在这种确定与不确定的张力中,为人类搭建起理解存在本质的诗意桥梁,让每个瞬间都成为通向永恒的入口。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网址:王顺天:为何作家喜欢怀旧|中原作家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166302
相关内容
台湾知名作家、“鬼故事大师”司马中原病逝,享年90岁李郁:诗人、作家、文学家|中原作家
作家们和《河南日报》的故事
“河南思客作家文丛”第二辑《涛自大海生》首发式在郑州举行
30篇访谈稿,还原当代女性作家的成长档案
作家班宇香港解读“季节为何漫长”:向前走,莫回头
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启动!即日起面向全球华语作家征稿
《淮阴作家》创刊发布会举行
草原喜欢,中原懂爱
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举办 王蒙获颁“年度致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