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回环往复的命运咏叹
剪刀的柄部是支撑部分,一般比较硬,不易弯曲。 #生活常识# #剪刀#
俞耕耘

约恩·福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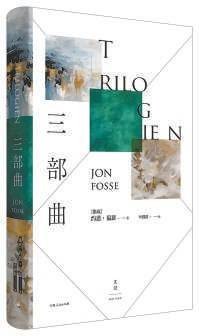
《三部曲》 约恩·福瑟 著 李澍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我看来,自己能获奖既是因为剧作,也是因为小说。在只写剧本的很多年后,我突然觉得好像够了,是的,有些过多了。我决定不再写剧本……我决定回到写作开始的地方,写散文体、写戏剧之外的体裁。”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在演讲中如此说道。
《三部曲》是他转向小说创作的重要果实,包含《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写作长达七年之久。此作以戏剧性的生活绝境为人性剖析提供了实验性研究。我将其描述为,置于荒原的生存危机。
小说人物的共性乃是缺乏身份、话语与社会角色。福瑟的书写带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气息:生而被抛,面对他者世界,感到异己且恶心。甚至,整个故事都有意虚化了具体时代的社会标记。仿佛可以移置在任何世纪的北欧,即使放在传说故事里也并不违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学生、被欺辱者,这类“边缘人”挣扎于生命的原始冲动中。其社会属性混沌不明,唯有通过危机(或罪行)才能揭示出人格特征。
阿斯勒和阿莉达,这对没有立锥之地的恋人,被迫出走他乡,来到比约格文。阿斯勒父母先后亡故,临时住所(船库)也被收回。农家女阿莉达被母亲嫌弃,无法在家中寄居。她偷了母亲的钱,告别家庭。我们为小说冷漠鄙陋的世界而震颤:无人同情,全然拒绝,没有住处,待产的阿莉达在湿冷雨夜蜷缩街头。有产者可以随意支配无产者的命运,并施加道德审判。小说高明处,是以情节实现主题隐喻。阿斯勒偷了船,才能“驶向生活”;卖了父亲的提琴(小提琴手的梦想),才换来婚姻的凭证(手镯);只有自己身死,才能成全阿莉达的后半生。爸爸西格瓦尔的话,预言了儿子命运——总是在离开。离开爱的人,离开你自己,“永远不能完整地属于自己”,“总是努力让别人完整”。
某种角度看,《无眠》具有安徒生式的幻灭,以及对于幸福的谵妄。沿街寻租,一次次被拒,像卖火柴的女孩划掉一根根火柴,全靠幻觉安慰。记忆里浮现亡父的小提琴和歌声,给这悲惨境地送上“协奏”。我很在意作家对悲剧何以发生的叩问。甚至,这种爱情是否也属于被迫的自欺?“现在阿莉达是世界留给他的唯一东西。这是他唯一的念头”“现在阿莉达怀了孩子,她和阿斯勒又没有结婚”。前者一无所有,后者别无选择,绝境使他们结合。作家先行预设了“被逐”与审判的语境:未婚而孕,偷食禁果,被逐乐园,对应无人接纳的惩罚。阿莉达的身孕,就像霍桑的A字,施加了荡妇羞辱。贫民所面临的残酷,是穷与罪的双重重压,如何负罪而活是小说探讨的核心。
福瑟很可能借鉴了三种故事模式:《罪与罚》里穷学生杀了老婆子;《悲惨世界》里冉阿让负罪逃亡,用新身份重塑自己;《无名的裘德》中夫妇与孩子走向了自毁。《三部曲》恰恰是三者的结合,阿斯勒既摧毁了他者(妨碍生存的人),也改换名字(变成乌拉夫),最终被一个老人告发而被绞死。这个老人就像雨果笔下的沙威,在珠宝店、酒吧和住所纠缠不放,如同抽象的审判,无处不在。至于如何指认罪行,则是小说的虚空。
我们只是从第二部《乌拉夫的梦》的逻辑线索,推断阿斯勒背负的命案:拒绝他们的房东老女人失踪,故乡的船库所有者被杀。从主人公生存权被剥夺的角度看,正是不公的环境才催生了罪行。正义的含混,常常是文学伦理潜藏的力量。“小提琴手的命运就是如此,一种宿命,那没有财产的人必须靠着上帝赐予他的礼物勉力维持着,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福瑟早已让阿斯勒的灵魂飞翔。那个自诩正义伸张的老头,只不过是贪婪卑劣者,反而遭到鄙视。小说中这种情感价值的倾倒,始终先于现实的价值判断。
《三部曲》是福瑟自戏剧转向小说的重要实践,作家自谓“慢散文”的风格。如何理解这种慢?它是对生活性的重现——关于生存的慢性体验。生活如同衰老,是缓慢的退行性改变,作家用语言的蔓延缠绕,模拟这种感受。语言常常在意识中出神,在时间里陷落。叙述变得绵延、附着而粘连。与那些意识流作家一样,福瑟有意省略标点,一逗到底,甚至不见句号。“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一个持续的流动过程中,一个不需要句号的乐章里。”他暗示叙述永无间歇,漫长的压抑无从切割。与留白相反,作家在努力填充文本叙述的空隙,扩张弥漫带来文学空间的高密度。
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境遇,甚至感官和意识都出现了诸多“偶合”。我并不认同诸多评论所言,福瑟采用了“重复的手法”。因为,重复就是主题本身,是无声表达的整体。它构成命运不可抗力的显示,家族不同代际之间的传导。重复通向轮回,生命之轮在几代人身上轮动。西西弗斯式无法跳脱,后代重蹈前代人的生活幻觉,同时形成叙事回环往复。任何叙事的变奏,只有在常量(主题再现)凸显时才有意义。
《疲倦》中,阿莉达的女儿爱丽丝遇见母亲亡灵,追忆超越时空限制。阿莉达在码头捡到阿斯勒买给她的手镯,之后嫁给渔夫奥斯莱克,重回杜尔基亚,而她对阿斯勒的爱延续一生。儿子西格瓦尔所拉的琴,正是继父奥斯莱克买到的阿斯勒的琴。爱丽丝只记得同母异父哥哥的琴声,哥哥在她很小时一去不返。我们有理由将这些情境再拟,视为戏剧典型环境的反复塑造。即使远离戏剧创作的福瑟,也始终依赖戏剧思维。他将无数巧合重组因果,把道具作用发挥到极致,把不同时空压缩成“共时在场”。
从结构特征看,重复本身隐喻了几代人的命运关系。我概括为人物的和声、感应与叠合。阿斯勒的琴声与阿莉达父亲的歌声,产生呼应联想。二人都在音乐里追忆亡父,他们相爱几乎复制阿斯勒父母的相遇,“爸爸西格瓦尔遇到西利亚妈妈的那个晚上也是在那儿演奏”;生下的孩子也与阿斯勒父亲的名字相同。命运对位,体验重合,极大增强了叙事力度。幻觉、梦境、记忆与潜意识,一起参与同构,也不应简单归于神秘主义。在我看来,作家意欲达成一种“情感结构”的跨时空贯通。他暗示人物的精神性从未随代际消逝,相反,它会以后代的生存为照见印证。从而,《三部曲》就形成了一唱三和,代代回声的命运咏叹,是对生命存在、爱欲信念的深沉探寻。(作者为书评人)
责任编辑:
网址:《三部曲》:回环往复的命运咏叹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30786
相关内容
《三部曲》:回环往复的命运咏叹故事与命运——约恩·福瑟《三部曲》读后
蔡崇达《草民》在泉州发布,故乡三部曲收官
蔡崇达携新书《草民》回到故乡,“故乡三部曲”历时十年收官
《封神三部曲》电影的角色宣传图来袭…
封神三部曲即将在六号揭晓神秘面纱…
《西北往事三部曲》研讨会在京举行
大有书局推出“梁晓声谈中国”系列三部曲
新书|看见那些渺小而伟大的人们 ——蔡崇达“故乡三部曲”终章《草民》出版
“马里乌波尔三部曲”终结篇,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