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
你知道什么是碳足迹吗? #生活知识# #环保常识#
原标题:伍尔夫: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

你可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吗?
大部分文学读者从《达洛维夫人》的日常叙事,《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主义思考,以及《到灯塔去》成熟的意识流写作中了解这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为人熟知的语调是沉思的、细腻的,大多时候更是私人的。
然而在她创作生涯的晚期——战争蛰伏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伍尔夫决心开启一次写作风格的转型:她逐步脱离私人化的文学,投身于为公众发声的写作。“文学界有伟大的老女人吗?”她问。她认为,男性的统治欲让所有人都成为战争的奴隶。所有人,包括男性自己,也需要从自己的“虚构观念”中解放出来。
最新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今天单读分享第十四章“公众之声”的节选,从战争阴云仍在的今天,跨越一个世纪的距离,聆听伍尔夫不得不选择公共写作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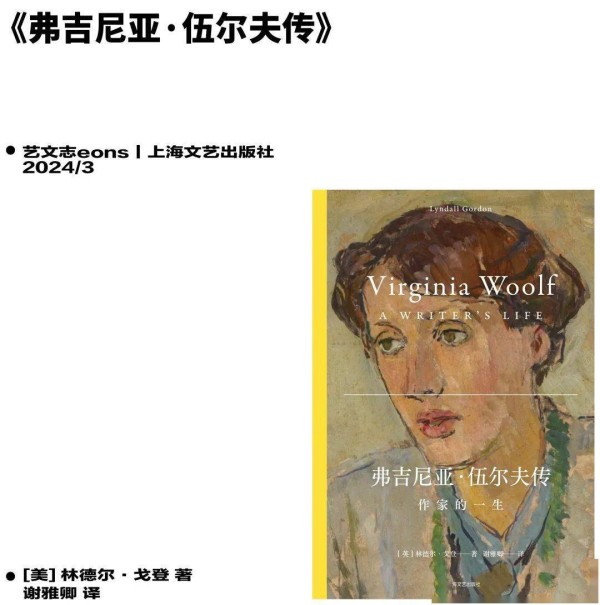
公众之声(节选)
作者:[英] 林德尔·戈登
译者:谢雅卿
乡村生活并没有让她进一步缩回自己珍贵的小世界中,相反,它使她尝试去挖掘战争带来的“群体情感”。“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强烈。”她希望从私人记录转向公共记录,从小说转向编年史,去展示历史的全貌,牢记在名人的行动中夹杂着的普通大众的种种行为。早在 1927 年 12 月她就意识到,为了了解无名大众,她必须不再沉浸于自我:“我的梦想太集中于我自己了。”从那时起,她就下决心“保持匿名”。通过专注于因为太普通而被忽略的家庭活动,她将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一种独特的女性声音,它将替代贪恋权力的政客们的叫嚷声。1932 年和 1933 年,她对《普通读者 II》和《弗勒希》(Flush)中那种低沉的、边缘化的声音非常不耐烦,急于结束这两部作品。她不愿相信自己只是个上流社会的空谈家,“这绝不是事实。但他们都这么说……不,我必须……创作,艰苦地、热烈地创作,因为我感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这样做”。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谈起过“某些改变,它们通常能让一个作家的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变得最有趣”。如果我们不是从销量上的成功(《弗勒希》《岁月》)来看她的写作生涯末期,而是从她未完成的或计划中的作品(《帕吉特家族》《幕间》《阿侬》和“奥克塔维亚的故事”),她的日记、谈话、随笔,还有最重要的檄文(《三枚旧金币》和《评论》[Reviewing])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即将改变自己的写作事业。她几乎一生都在为一个小圈子写私人的、挽歌一般的作品,而现在,她正在寻求一种代表公众的声音,向全民族的读者讲话。简而言之,伴随年龄的增长,她渴望成为民族良知的仲裁者,成为她所判定的民族财富的保护者。这似乎是个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挺身而出直面论战激烈的三十年代十分符合她勇敢的性格。“文学界有伟大的老女人吗?”她问罗斯·麦考莱(Rose Macaulay),“还是只有伟大的老男人?我想我应该准备好成为英国文学界的伟大的老女人。”
做一个“局外人”等同于“精神信仰的转变”。这意味着把自己从男性和女性的虚假义务中解放出来,而去发现女性全新的社会职能:去抵制战争,并且,按理想的情况,在遥远的未来禁止战争。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
1940 年 8 月,当德军的轰炸机每晚都盘旋在罗德梅尔上空时,她不再相信战争宣传——它们把对权力疯狂的爱归咎于某个偶然出现的怪胎。她重新阐释了克拉彭派对奴隶制的讨论,她指出,不论我们是什么国籍,都已被“男人潜意识中的希特勒主义”所奴役:那是一种统治欲。“奴役”这个词也在她的《和平——空袭中的思索》(“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一文中回响着:“如果我们自己能从奴役中解脱,我们也就能将男人从暴政下解放。希特勒们是靠自己的奴隶喂养大的。”对于战争年代受到权力支配的读者来说,她富于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看起来很荒谬:我们必须激发创造性情感,这种情感将取代战士们被煽动的对施虐和勋章的狂热,取代他们膨胀的荣誉感和手中的枪。
克拉彭派成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坚决反对奴隶制,和他们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把目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转向文明的永久弊病上来。她的曾祖父曾写过一篇言辞激烈的反对奴隶制的檄文;她自己也写了一篇批判战争制度的文章。她正直的脊梁骨更硬挺了。她的文章同样乐于使用直白的言辞,也有同样的信念,那就是领会了更高真理的人必须亲自去传播福音。
“我们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她在 1940 年问朋友希娜(西蒙夫人),一位曼彻斯特市议员。“我们怎么才能改变斗鸡的鸡冠和尖喙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能获得声望和赞赏,就会放弃荣誉,而去培育那些目前发育不良的东西——我指的是自然幸福的生活。”
1931 年 1 月, 她在女性服务协会(Society for Women’s Service)发表了一次演讲,受此鼓舞,她想续写《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续作将包括一系列涉及教育、性别和政治的论辩文章。1932 年,她开始动笔写一部“随笔小说”:她的计划是让随笔和说明性的虚构场景交替出现。小说的场景设置在中产阶级家庭帕吉特家族中,故事开始于弗吉尼亚自己出生的年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笔的部分最终被弃用了(而小说部分后来成为《岁月》),但它们都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随笔一样,充满开创性言论。她们二人都渴望挖掘女性的真实天性;都宣称不工作会让女性的思想变得浅薄。弗吉尼亚·伍尔夫进一步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们琐碎的嫉妒心,她们被禁闭在家庭的牢狱中,唯一的出路就是结婚。而更隐蔽、更难补救的是对性的恐惧。她指出,小说中那个颇有才能的女孩兼具叛逆与顺从,因为她接受了主流秩序,必须学会怀疑与服从。
随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分析了一个在牛津大学读书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年轻男子相对应的扭曲心态:爱德华·帕吉特接受的教育让他对表妹吉蒂·马隆的自然反应发生了偏移,变成对工作和锻炼的狂热,如果继续下去,还会变成让女人心灰意冷的情感理想主义。当爱德华为吉蒂写了一首希腊语诗时,他根本没有把她想象成真正的女人。事实上,他那训练有素的情感本质上是自反性的,是自我崇拜的。

电影《赎罪》
分析的光束最终照到了吉蒂身上,吉蒂被禁锢在父母对上流社会女性形象的虚假观念中,这让她远离自己天生的兴趣。她知道,她喜欢农业,但她只能在幻想中逃避现实。作为沃顿的女儿,她的举止礼仪无可挑剔,但隐藏在背后的是她对牛津男人们的厌烦,因为和那些人聊天时必须谈论他们本人。她暗暗被一位朋友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坦诚打动了,那个家庭对女儿和儿子怀有同样的期待。她还受到她的未婚家庭教师的鼓舞。尽管这些人在权力体系中都无足轻重,却反映了吉蒂可能成为的其他形象。
“帕吉特”随笔是根据 1931 年演讲的笔记写成的,它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女人总在接受一套与自己的价值观多少有些偏离的价值体系。弗吉尼亚·伍尔夫警告职业女性,她说,即使对她们而言,找到自我也依旧任重道远。她们自己的价值、梦想、情感,都会遭遇嘲讽。她想象了一个充满优越感的男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女仆在书房里惬意地阅读柏拉图的书,而女厨正在厨房里创作一曲降 B 调的弥撒曲。于是,他严厉指责了仆人们作曲或阅读柏拉图的行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告诫女人们不要愤怒,因为愤怒是内心的敌人,“它总是消耗你的能量,毒害你的幸福”。她的忠告是:“保持耐心;保持愉悦。”
演讲那天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同台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女爵,她曾作了一首D 调的弥撒曲。这位七十一岁的前妇女参政论者、作曲家和弗吉尼亚成了朋友,并帮助她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证明她的想法是她们共有的,通过她自己直率大胆的言语示范,以及最重要的,通过召唤出弗吉尼亚为她的小说保留的另一面。在 1930 年 5 月 2 日的第一封信中,埃塞尔说:“我从不觉得……我看见的你是真正的弗吉尼亚,因为……我只看本质。”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弗吉尼亚,不同于她的许多密友为我们描述的那个纤弱、疯癫、爱开玩笑的表演家:埃塞尔看到的是“战斗的兆象”。她唤醒了弗吉尼亚那属于战士和改革家的一面,而激发它的力量源自弗吉尼亚对母亲——女性力量的象征——的忠诚。“我体会到的最强烈的情感……就是对母亲的情感,”埃塞尔写道,“三十八年前她就去世了,每当我想起她,都能感到真正的激情;欢乐、温柔、怜悯、敬慕,还有痛苦……”埃塞尔还唤起了弗吉尼亚不顾一切对抗死亡的精神。1930 年 8 月 11 日,埃塞尔巧妙地拨动了这根弦:
不论多么生动的体验都无法从我身上剥夺这一点——我爱、我爱死亡——我愿脱离俗世——我爱(普罗提诺所说的)把永恒与现世分离的观念……
埃塞尔和之前的薇塔一样,也爱上了弗吉尼亚,弗吉尼亚让她们两个心神不宁,自己却始终忠于伦纳德。面对薇塔的时候,她滔滔不绝,故作姿态;而面对和她观点相似的埃塞尔时,她以无拘无束的坦诚写了许多信。埃塞尔讲话时就像“未被阉割的猫”一样跳脱、吵闹、直白,把弗吉尼亚从她混合了健谈和矜持的性格中解放了出来。我想,弗吉尼亚从未对任何人用如此不经思考的方式说话。尽管她的回信带有调侃意味,也巧妙回避了可能引发混乱的约会,但她显然很享受摘下面具的感觉。她欣赏埃塞尔的勇气和公共意识,以她为基础,弗吉尼亚创造出了《岁月》里的妇女参政论者罗斯。埃塞尔直言不讳的作风与弗吉尼亚所受的保持沉默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1931 年,她在一封给埃塞尔的信中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认识你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心想,这是一位能说会道的人。他们不知道感觉是什么,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最尊敬的每一个人都是沉默的——妮莎、利顿、伦纳德、梅纳德:他们都很沉默;因此我也把自己训练得沉默寡言;导致这种沉默的原因还有我对自己那无限的感受力的恐惧……
她继续问自己,她习惯性的沉默是否源于她对“潜伏在表层之下的未知力量的恐惧?我从未停止过这种感觉,我必须脚步非常轻地走在火山顶上”。
埃塞尔回信说,她对那座火山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每时每刻都知道,冻僵的猎鹰栖息在大片炽热的岩浆上。”她过于热情地写道,“暂停一会儿吧——别让臀部那么僵硬”,并继续说:“我总是想象,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一定曾在穿过树丛时将树木点燃,你赤脚走过岩石和墙垣,为自己开出了一条路。”她明白火山的危险——“我已经看到你脚下的地面有了细微的裂缝”——她也明白,按照惯例,我们需要掩饰危险的迫近,但她还是鼓励她说出来:
你知道的,弗吉尼亚,我强烈地感受到……一旦[女性]摆脱了男性观念对她们的影响,某种带着光和热的新事物就会在世界上传播开来。

电影《时时刻刻》
弗吉尼亚·伍尔夫 1931 年的演讲稿的确尝试了一种直白有力的新语言风格:
如果我现在写书评,我会说[战争]是一场愚蠢的、暴力的、可恨的、白痴的、无足轻重的、卑鄙的、恶劣的表演。我会说我对战争类的书籍厌烦得要死。我痛恨男性的观点。我厌倦了他们的英雄主义、美德和荣誉。我认为这些男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别再谈论他们自己。
1938 年,当《三枚旧金币》出版时,她构想了一种“漠然”策略。局外人(她坚持认为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局外人)必须漠视男人的雄辩、自大,尤其是好战:
她会说:“‘我们的国家’在她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把我当奴隶对待;它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也剥夺了我拥有它的权利……所以,如果您坚持说你们作战是为了保护我,或‘我们的’国家,还是让我们冷静地、理智地说清楚:你们是为了满足我无法共有的性别天性而战;你们是为了获得我不曾并且将来也不可能共享的利益而战……”
《三枚旧金币》是写给“某位先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想象中的公众从职业女性扩大到了受过教育的男性。在 1931 年的演讲中,她机敏、从容又充满感情地同女人们交谈。而现在,她以冷静而耐心的礼貌态度对“某位先生”说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说服听众,而不是像《一间自己的房间》那样消除听众的敌意。《三枚旧金币》理性地审视了支撑父权制律法的那些可疑的情绪、未说出的假设和含混的言辞。她使用的是该律法本身的方法,即长篇累牍地论证有事实支持的论点。对于女性读者来说,这种冗长的论证是不必要的,不过,脚注中的材料很吸引人,而她对十九世纪女性更为隐蔽的抗争所做的分析同样精彩,比如,她分析了决心学医的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Blake)和中年时违背父亲意愿、不肯嫁给他的牧师的夏洛蒂·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最令人生畏的斗争不是与外部的斗争,而是与自己、与那些根深蒂固的让女性贬低自我的观念的斗争。
她指出,男性也被自己的虚构观念奴役着。他让自己变成工作的奴隶,只为保护他想象中的无助的女人。他以同样的虚构观念煽动战争狂热。恶性循环便持续下去:为了索取对这种自我强迫的补偿,他变成一个“对同情上瘾的人……要求补充精神能量;或像希特勒所说的,一个需要休整的英雄;又或是像墨索里尼说的那样,一个需要女侍包扎伤口的士兵”。一条脚注提到,英语文献中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我从来没有犯过把女作家看作严肃的同类艺术家这样的错误。我只是把她们看作具有敏锐的欣赏能力的精神上的帮助者。她们可以帮助深受天才折磨的少数几个人欣然忍受苦难。所以说,她们真正的作用只是在我们流血时给我们拿拿纱布,给我们用凉毛巾擦擦额头。如果她们那富有同情心的理解力真能有更浪漫的作用,我们会多么珍惜她们啊!(威廉·格哈迪著,《一个多语者的回忆录》,第 320、321 页)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让女性就职于教堂、证券交易所或外交部门的提议依然遭到强烈阻挠,这“敲响了我们身体里的警钟;一种交织在一起但又非常喧嚣的吵闹声在重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你们不能……”
她开始写《三枚旧金币》时,心里平静地相信,五十五岁的自己终于“走了出来,把伪装扔在一旁”。1937 年夏天,她怀着狂喜的解脱感写下这篇文章,感觉自己“像陀螺一样在丘陵上旋转了好几英里”。她构想了一种投票权,它不是为了支持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反对整个权力体系,她说:“我觉得自己至死都享有投票的权利,我摆脱了所有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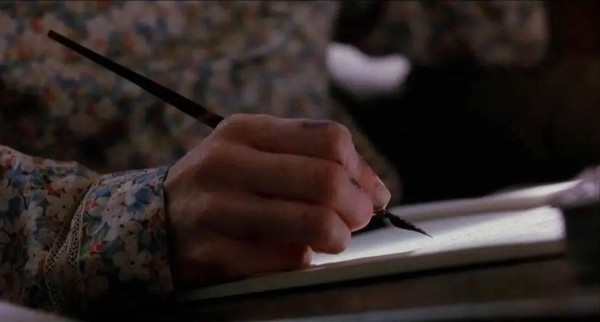
电影《时时刻刻》
《三枚旧金币》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弗吉尼亚·伍尔夫因此被称为英格兰最杰出的檄文执笔者。这本书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但伦纳德一直对其态度冷淡,她的大多数密友,比如梅纳德·凯恩斯和薇塔,也都对这本书不以为然。昆汀·贝尔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我亲爱的小姨到底想要什么呢?……没有人想打仗,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做了想做的事,也就是出卖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让他们变成奴隶,以换取几个月心惊胆战的和平,哦,这样做可真是种解脱。人人都害怕极了,到最后,我们只能战斗,因为除了自己,已经没有人可背叛了。当法国人那样做时,我们惊慌失措,像困兽一样战斗。在其中,我看不出女人比男人更好战或更不好战,而且,对于军事荣誉这个概念,除了不怎么了解 1914 年战争的老埃塞尔夫人和其他保守派的上流女士,没有人有任何想法。”
看起来,和平主义的反对者们担心即将到来的希特勒势力是对的,他们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探讨的是“一战”中过时的问题。不过,如果跳出 1935 年至 1939 年的历史语境来看,她反对统治集团纵容男性暴行的观点对何时何地发生的战争都适用。当时,她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她曾说,在《细察》(Scrutiny)杂志上受到攻击并被朋友们送去考文垂是一种有益的解脱:“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感到背后有一堵墙支撑着我。不过逆着潮流写作有种奇怪的感觉:完全无视潮流是很难的。但我一定会这样做。”
(上文摘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
由艺文志 eons 提供)
▼
2024 单读全年订阅首发
在复杂中寻求心灵的解放
责任编辑:
网址:伍尔夫: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8297
相关内容
伍尔夫:下一个任务难道不是解放男人吗?这次难道我还是没能在上桌时领先所有人吗?
这难道不是戚薇本人吗?
唐嫣不是上海人吗?为什么还要胡歌教她上海话
这确定不是在演我本人吗?和不嗑「喜追风」CP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导演和演员间的默契,难道不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吗?
九头妖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你捏脸,这份温柔难道不是爱吗?
小师侄疑惑道:“我难道不是最亲近的徒孙吗?看来我要真的发飙了!”
单依纯难道不是薛之谦的克星吗?三年后再掀“创飞”热潮
《山花》2023年第5期||谢雅卿《花岗岩、彩虹与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