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作家?科班出身的焦典用热情将天赋与知识打通|当代书评·专访
如何处理家具划痕:使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后,涂上与家具颜色相近的色蜡或专用修复液。 #生活知识# #家居#
原标题: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作家?科班出身的焦典用热情将天赋与知识打通|当代书评·专访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焦典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清晰志向。读小学一年级,还什么都不懂,她就在班上愣头愣脑地跟同学宣布:“以后我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她写了一篇“情感真挚的虚构”作品,拿给奶奶阅读,出乎她意料的是,奶奶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时隔很多年再回去,奶奶还会拿出来,拿着一张纸读”,奶奶成为她最初的读者。她爷爷是云南一名地质勘探队员,给她讲了很多云南高山丛林里的故事。她希望自己有一天把它们写进自己的作品里。云南老乡、著名诗人于坚有一首诗叫《尚义街6号》,被她读到了,“觉得挺酷的,风格挺先锋。我曾经就在他写的昆明那条街旁边住过。现实与文学产生了对照,感觉很奇妙。”于是她就开始写诗了。

焦典(新经典提供)
2014年,18岁的焦典从云南曲靖一中考入北师大文学院,朝着实现“大作家”之梦迈进。2018年,焦典以优异成绩本科毕业后被保研继续在北师大攻读“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的硕士。这一专业实行双导师制,她的导师,一位是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另一位是资深文学评论家张柠。2019年,作家毕飞宇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驻校期间,开设了一堂特别的写作课。在课堂上,他选择了焦典的小说《黄牛皮卡》为点评底本与学生们一起讨论。在课后,毕飞宇继续指导焦典,帮助其完成小说的两次修改。《黄牛皮卡》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毕飞宇对《黄牛皮卡》小说创作进程的讨论也在同期发表。
2021年5月,“2020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文理学院举行。焦典获得了“年度大学生奖”。封面新闻记者当时就在颁奖现场,与焦典有过一次深入的对话采访。当时的焦典刚刚硕士毕业,又考到莫言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采访中她特别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渴望,“生活是一场搏斗,写作也是一场搏斗。或许直到最后,依旧会和《老人与海》里的圣地亚哥一样,拖回岸边的不过是一架空空如也的鱼骨,但至少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勇敢又无所畏惧地搏斗过。”

《我在岛屿读书》节目海报。图中上方为焦点和莫言
在校园里,焦典一边按部就班上课、阅读、写诗,一边又开始小说创作。2021年11月26日,由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与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全球发展与展望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京师-牛津‘完美世界’青年文学之星”评选揭晓。在这个终评评委团由李敬泽、张炜、叶兆言、格非、毕飞宇等组成的奖项中,焦典因短篇小说《六脚马》获得唯一的金奖。2023年,包括《六脚马》等在内,焦典近几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上的多篇小说被结集成书《孔雀菩提》,由新经典&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得到业内和读者的好评,出版五个月加印五次。网上有读者评论,“好像找到我的年度小说了。”在余华、莫言等作家参与的《我在岛屿读书2》中,作为青年作家之一,焦典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中。
现实是“迷宫”,小说和诗歌是可以“飞起来”的竹蜻蜓
虽然在北京求学多年,但云南始终是焦典精神世界的重要版图。这从她的小说集《孔雀菩提》就可以看出:云南特色非常鲜明,被称为是“春云般清澈蓬勃”的云南雨林故事。她借边地题材,表达她关于人的生死、信仰、尊严的思考,深入地探索人的心灵世界。在其中一篇《木兰舟》中,她写一位傣族老人对生活与生命的达观。这位70多岁的傣族老人,一辈子在喝酒中享受着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智者。在《鳄鱼慈悲》中,她写一个在云南大山里为寻找矿藏行走了一辈子的老人,面对衰老与死亡时,内心的倔傲与不屈、牵挂。焦典的小说中,对女性的生存与命运给予了比较多的关照,《六脚马》是一篇将苦难的人生化为在想象中腾飞的故事。小说中四个底层妇女经历了被拐卖、家暴、逃跑、拼命挣钱养家的艰辛,想逃离,最终也无路可走,现代的摩托并不能带她们逃出大山,脱离困境,寄托于想象的六脚马带她们飞向远方。
焦典的小说写得似真似幻,处于想象与现实交汇的边缘。这跟她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密切有关。云南小寨的那些神秘故事,儿时,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爷爷,总是会给她讲述许多关于金沙江、山林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说,焦典对那样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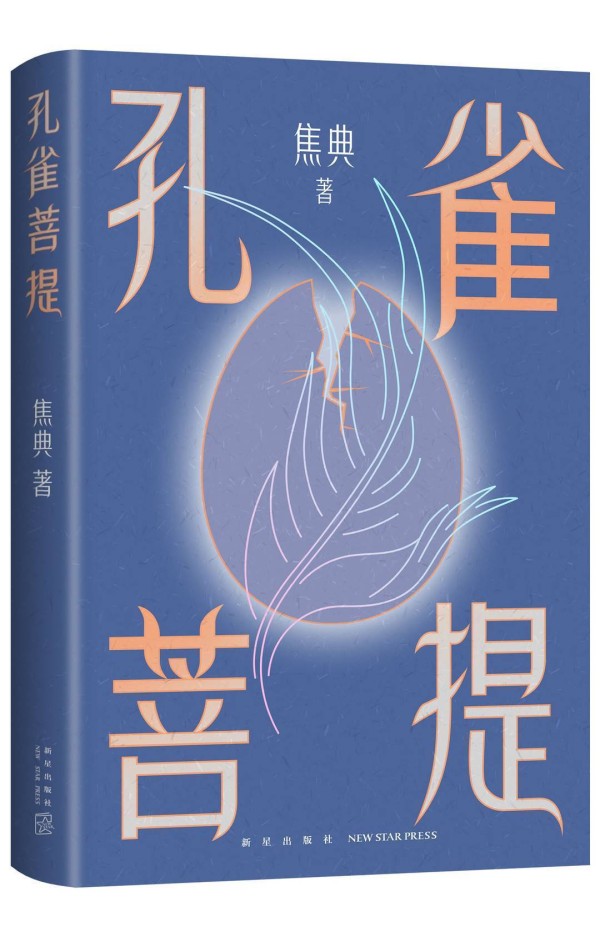
《孔雀菩提》
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云南没有海。但如果你走到山的尽头,往下眺望,山峦起伏,层层叠叠,如果这时云的流速再快一点,如果这时再有一阵风,那坚定不移的山也会流动起来,深绿的浪压着浅绿的浪,一层一层地涌到你的脚下。那种眩晕感,那种没来由地想要一个猛子扎下去的冲动,和站在海边时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云南有海吗?我都会说,有的。虽然我都省略了后半句——只要你站在山的尽头。”
此外,把小说写得“飞起来”也跟她一个艺术理念相关。她将强大的现实生活视为“迷宫”,而走出“迷宫”的最好方法是“飞起来”,“我很庆幸在这生活的迷宫之中,我手里还握着诗歌、小说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蜻蜓。当你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拥有一定的经验,仅凭手里这用寥寥几个词语、几句诗句组成的竹蜻蜓,你就可以飞起来。”小说也不只是讲故事,同时写诗和小说的焦典,对小说中的语言不能不讲究。她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是地方性的语言与普通话的融合。这种语言具有陌生化效果,但它同时又能让大多数读者读懂。《人民文学》的编辑,也是《六脚马》的责编梁豪说:“这是一篇可以看语言的小说,或者说,是被语言挑动起来的小说。”
导师莫言点评:“焦典在小说的修改方面表现出来的领悟力,是让我既欣慰又羡慕的”
作为焦典的导师,莫言为《孔雀菩提》写了一篇序文《根植沃土,仰望星空——读焦典小说杂感》。文中他提到,“焦典的小说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这是我阅读她的第一篇小说《黄牛皮卡》时得到的印象。这篇小说得到过小说行家毕飞宇的指导,我想他的指导应该主要是在情节的合理性与人物的行为与性格塑造之间的关系方面,而对形成了她的小说风格的方方面面,则给予了保护与激扬……后来她考了我的博士,严格地说,其实我们更是文友的关系。一个老作家的经验,也许就是他的局限,而一个年轻作家的弱点,也许可能发展成她自己的特点。这几年我们谈小说的机会并不多,但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焦典在小说的修改方面表现出来的领悟力,是让我既欣慰又羡慕的。”
对于这棵文学好苗子,莫言也不吝赞美,“焦典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作品的数量也不太多,但已经露出了峥嵘头角。这部小说集展示了作者的个性和才华,如果让我来用文学的语言简介这部作品,那我要说:“这部作品像孔雀一样华丽,又像鸵鸟一样朴素;像小猴一样活泼,又像大象一样笨重。在密林,在边城,在山寨,在现代化与传统民族文化混合生长的地方,人物在其中如鱼得水般地生活着,有痛苦,有欢乐,有爱情,有仇恨,有难解之题,有希望之光。我希望并相信读者会比我读出还要深刻还要丰富的东西。”
对话焦典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再次与焦典有一番深入对谈。距离上一次采访已经3年过去了,焦典在莫言门下也已经读到博三了。她有哪些突出的收获?与其说,我们追踪的是一个青年进步的脚踪,不如说,我们想更弄明白,一个热爱文学写作并有足够天赋的年轻人,是如何透过系统、专业的文学创作培养课程和她自己的勤奋、专注,一步一步修炼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写作者的。
近些年来,关于“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这个话题,一直都有讨论。常见的观点是,成为一名作家多被认为是天赋的因素更多,而系统的中文教育可能更适合当学者。但焦典,却让我们看到,当天赋、兴趣与科班出身、师出名家结合起来,起到的是优势叠加的良好效应。她用热情把天赋和知识打通了,走在实现“大作家”的坚实路上。
焦典在顶级的学院象牙塔里,一直积蓄着自己,不喧嚷不急躁。她经常穿绿色的衣服,很像一个刚从丛林里走出的少年,元气淋漓。从本科到博士,她已在北师大连续读书10年,还未完全踏足社会。但并不代表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她有自己的忧思。“学会面对这样日益复杂、缠绕、令人眩晕的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我们这代人的必修课。更为重要的是,迷宫已经是我们的精神体验和经验结构。看似有无数的选择,有无数条分叉路,但事实上留给每一个普通人能走通的路又有多少呢?”
对于视频与文字的张力关系,她这样分享自己的体验,“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在2022年的年轻人,视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经常会用视频学习一些新东西,比如看视频博主教弹尤克里里,学习怎么游自由泳。很多技能性的内容,单看文字可能比较难以掌握。”她认为,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视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能并且也应该激活人们重新体验生活的愿望,而不是成为生活的替代品。而且,文字的艺术绝不会消失,因为文字是对想象力的训练,是真正的扩展意识的训练。而视频很大程度上,消灭了某种想象力,消灭了属于你的独一无二。“视频是填充,尽可能地填充所有的缝隙。文字信息的接收需要调动想象力,阅读空白,领悟并未被说出来的信息。”对于人工智能给文学写作带来的冲击,焦典也淡定并乐观,并靠靠未来也会考虑使用AI作为自己写作的助手,“如果它能帮忙把小说写得更好的话,何乐而不为呢?人类作者在一些地方可以在机器的帮助下,节省时间,从而可以更集中精力去做需要突破原创的精华部分。”
“专业的文学教育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同代人共同成长的经验”
封面新闻:从本科到博士,你接受了系统的、顶尖的中文系专业文学教育。如果让你自己剖析一下,你觉得这对你的文学创作来说,具体的助益有哪些?
焦典:相比起知识或者技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专业的文学教育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同代人共同成长经验。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写,一起读,一起交流,一起修改,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重要和美好的。写作有出处,有师法,有脉络,这些在文学研究中是经常被关注的。但是写作还有一个横向的面,就是我们的同代人。在实际的写作中,大多数时候,这个同代人的支持,影响,喜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写作。至于可能性,我们的老师也说,我们这代人普遍来说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更丰富的资源,我觉得这些积淀未来是有很大可能绽放出多色彩的,多形态的,在精神层面更幽邃的作品。
封面新闻:你的校园生活,一般是怎样度过的?基本都会做些什么?
焦典:在学校里,我一般就写写东西看看书,最喜欢的是去游泳和打球。
封面新闻:莫言先生是你的导师。不管是读其作品,还是跟他本人来往,听他讲课,这几年你觉得都有哪些比较大的收获?
焦典:老师教会我沉默。刚入学的时候,得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奖学金,跑去和老师“炫耀”。老师回复我:保持淡定,自己高兴就好。所以要说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学会在一些时候,少说话。
一条黑色长裙的边缘是擦亮一篇小说的火花
封面新闻:请你分享一下,你的一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会不会是先有一个人物形象,还是先听到一个故事,触动了你,然后你要展开联想,然后想一下整体结构?
焦典:小说的创作一般是,最开始出现一个小小的火花。小小的,摩擦生火,“擦”地一下,照亮一小片地方。比如,《六脚马》这篇小说,那个小小的火花是一个秋天,从大衣的底部边缘露出来的裙边,那个弧度很美。裙边是黑色的,一条黑色的长裙,和好多年前,我妈妈坐上搬家的卡车时穿的一样,卡车黑黑的大肚子里装着很少很少的一些行李,和妈妈。我记得我们都没有哭,我妈装作小孩子的样子,跟我挥手说拜拜,我装作大人的样子,跟她挥手说拜拜。卡车开走时的尾气也是黑色的,看来是质量不怎么样的车。也和很多年前在一个重要面试的等候区见到的一样,说了两句话就告别,直到相隔了好多年又再次遇到了。脸、声音,什么都不记得了,但竟然还记得黑色裙子的纹路。 很开心,也很伤感。看着看着,黑裙子就飞到眼睛里,眼睛里也黑黑的。那么多时刻积攒的泪水,忍住没有流下的泪水,没有道理和立场的泪水,就从《六脚马》里的那个女人眼中流下来了。“眼睛里黑黑的,像要下大暴雨。”
封面新闻:你的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着墨较多。作为女性存在者,你在写作的时候有特别注意到性别吗?在日常生活、思考事件和判断世界中,性别角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
焦典:我不需要特别注意性别,因为我的性别天然决定我必须看到“性别”。性别视角无时无刻,比如一枚瓶盖,一枚小小的瓶盖,它在设计的许多时候就已经超过了部分女性的扭力矩,你会求助别人帮你拧开,然后这种行为容易被嘲笑为“绿茶”,然后你就用自己的衣角,或者一张餐巾纸,包裹住它以增大摩擦力。你就像这样,一次一次地,努力,仅仅是因为瓶盖。或者你因为久坐而腰酸背痛,想买一把符合人体力学的椅子,然后你发现即便靠枕部位调到最低依然无法够到,你的身体在这把也许非常昂贵的号称充满了科技与人文关怀的椅子上依旧酸痛,因为它们本就按照男性身材设计。或者你喜欢音乐,你多么想学会弹钢琴啊,你的手指在黑白的琴键上跨越,如果够不到的话,再努力一点吧,把手指打得更开,这会痛,但是这是必需的,因为它的琴键也本不为你更为纤细瘦小的手掌设计。凡是不能仅仅用性别去解释,但凡事我们都将看见性别。
忠于词语 “让小说的语言也拥有诗的品质”
封面新闻:你既写诗,又创作小说,都取得很好的成绩。你如何看待诗歌、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区别与联系?对你来说,一首诗的灵感和一篇小说的灵感,其到来和被你抓住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焦典:我只能说我以我自己的创作来看,诗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小说更多的是一种故事。诗歌是点与点的汇聚,小说是线与线的编织。诗歌是一棵老树,立在吹了很久的风中,小说是那阵吹了很久的风,在大地上划过的轨迹。至于灵感,我觉得灵感不是金苹果,等待着,等待着,“啪”地一声掉在你的头上,而是一个搭建编织的过程。整个过程就像在野外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方圆无人,只有寂静。从外面捡回去一个破烂的渔网,一个没有小鸟的鸟笼,一把刀柄折断的匕首,或者,什么都没有捡到。只是带回去了一身的柴火味和泥巴。然后坐在屋里,一点点的收拾,把它们修补、擦亮、组合,并且就凭借这些被别人丢弃了的碎片,关键时刻点燃了它们,看它们小小的火光,可能别人都不稀得看的火光,跳跃着度过了漫长冬日。
封面新闻:我读你的小说,特别注意到你的语言。词语地道、腔调不乏幽默以及恰到好处的诗意。你此前在成都领取过星星诗刊的大学生诗人奖。在诗歌写作领域取得的经验,会用到你的小说写作中吗?

焦典(右1)2021年5月在成都领奖(张杰摄影)
焦典:是的,我确实有意识地想让小说的语言也拥有诗的品质,我始终认为,文学还是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即便是“讲故事”的小说也应当如此,而诗无疑是语言锤炼的最极致的艺术方式。一篇小说,如果上来就“老铁,666啊”,或者就是那些已经被咀嚼过无数次的陈词滥调,什么“她的眼睛笑得像弯弯的月亮”“他的嘴角划过冰冷的微笑”……那不管你写的是多么壮阔的一个故事,写你上了太阳,逃出了银河系,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丢到垃圾桶里的文本。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一定要优美或是精炼,而是要具备一种语言的品格。就像莫言老师的语言,是一种爆炸性、万花筒般的语言景观,金宇澄老师的《繁花》的语言,是上海方言那种细碎连绵的语言。语言是一个作家风格最鲜明的外衣。比如莫言老师曾经分享过他的老师徐怀中说过的一句话,语言就是一个作家的内分泌。最初是语言,最后还是语言,我是这样认为的。
封面新闻:你如何理解语言风格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焦典:诗歌写作锻炼了对词语的斟酌和谨慎。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帕斯,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忠于词语。每一个词语就像是一颗颗种子,诗人的任务就是把语言固化的、僵硬的土壤翻松,然后把词语的种子种下去。当然,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语言的土壤经过漫长的损耗已经布满了坚硬的石头,词语这颗种子要想生根发芽,必须要对土壤进行一番大清理,亦或者,种子本身要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而当我把这些精心淘洗过“词语”放置到小说中时,它们经常能带来一些惊喜。
云南是我的“烙印”
封面新闻:你的文学作品中的云南特色也很迷人。故事发生的地方都是云南。你从云南到北京上大学,一路读到现在博士三年级。对你的创作来说,云南给你带来了什么?请您概括一下呢?
焦典:小时候在一本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讲小鸡仔的“烙印现象”,说的是小鸡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生物,就会被它认为是自己的母亲。云南是我的“烙印”,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它的低低的云,是它薄而脆的风,在晾晒的床单上留下了好看的形状,出生时我看到了,所以我不会再忘记。柏拉图在《论诗的灵感》中说:“我们将不会终止我们的探索,我们所探索的终结,将来到我们出发的地点。”小说同理,文学同理,甚至我们的人生可能都同理。走啊走,走到最后,抬眼一看,还是走回了出发的地方。云南选择了我,云南带着它的气息和故事,向我走来。云南像一根透明的绳子,绑在身上,或紧或松,有时越缠越紧,有时咔嚓一下,以为给它剪断了,其实回过头它还在连着。
封面新闻:在北方的多年生活,对你带来哪些启发?
焦典: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北京,到现在都十年了。北京很好,有我爷爷爱看的升旗仪式,而且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云南,我们小时候其实骑自行车的不多,因为山多,地就是上坡下坡,在云南不说东南西北,说上面下面,往上面走,往下面走。同样的路,来回时间不一样,因为下坡省力,出溜一下就冲下去了,就和朋友比谁跑得快,你就看到一群人,跟原始大猩猩似的,嚎叫着从坡上往下冲,有笨的,就摔倒滚下来。上坡费劲,爬满头汗。但是有点人生哲理,因为爬上去之后有时候正好能看到夕阳,和放学下班的人成群结队地落下。而且,你知道,你家就在坡上面。但北京好骑车,特别一到高峰期,四轮的不如两轮的,两轮的不如生物能的。在北京的时间久了,好像确实很多东西就变了,所以有时候我说云南人都有点心虚了。同学去云南昆明旅游,问我,诶,你家这边哪家店好吃啊?我就给人家哐哐一顿推荐,结果人家发信息来:没有这家店,已经倒闭……本科的时候从火车站打车。快到地儿了,司机问我,是这儿吗?我说,再往上面走走。司机说,什么上面?哪有上面?我一愣,是啊,这里哪有什么上面下面呢,四面八方,平原如此开阔。
在拼命地创造“有”的时代,文学创作“无”和“空白”
封面新闻:你是一直在文学高度相关的系统里生活,生活中文学含量很高。但与此同时,很多人过着离文学世界比较远的生活。大家忙着赚钱、工作、交友、娱乐、刷短视频、追星、追剧等等。严肃的(与娱乐性质相对)的文学其实并不占太多份额。对此你有怎样的感想?
焦典:是的,娱乐、刷短视频、追星、追剧,其实我们现在是更丰富了。但是视频,游戏,各种娱乐,它们是在消灭空白。世界本身是张白纸。人本身也是白纸。我们的生活在上面留下痕迹,但在没有痕迹的空白处,才保留着世界和人本身的秘密。就像罗兰巴特说的“身体的最动欲之区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么……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迷神离”然后比尔·盖茨开创了电脑软件时代,并且说:“我们大家都致力于消灭纸。”现在是在尽可能地填补空白。填补日常生活的空白间隙,填补文化艺术的解读空白,填补思考停滞的空白。高分辨率、高像素、高帧数、低失真、舒适的峰值信噪......在拼命地创造“有”,以此来消灭空白的“无”。但是空白被消灭了,“无”被消灭了,那想象力也就走到了尽头。我觉得我们已经不缺少色彩、味道、触感,不缺少知道了,我们缺少未知,缺少空白,缺少“无”。而文学,创造了这种“无”。它的“无”将永远带给我们去追问和探寻的渴望。
封面新闻:你是否相信,人制造的智能机器最终能写出整体上超过人类作家的优秀作品,从而让人类的文学写作从整体上被超越?还是说,很长时间内应该没有这个可能?
焦典:如同第三个问题所回答的,如果有一天人制造的智能机器,它玻璃质地的黑色眼珠里也流出了那样的泪水,那我认为它已经和我们一样,并且也终将超过我们人类。
封面新闻:很多人都体会到,受到刷几十秒长的短视频负面影响,现在连长一点的视频都不怎么有耐心看完,读严肃一点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觉得注意力难以集中。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焦典:我自己的感受还好,反而是过于碎片化的东西,会让我觉得难受。比如一个新闻,我很想看到类似特稿那种全方位的,包括对当事人的心理勾勒,对事实的分析判断的东西,而不是两行黄色粗体的大字,使用吸引眼球的夸张措辞简约概括。如果说困扰,可能就是一种现在普遍追求的“短平快”风格,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我们太害怕了,害怕“慢”带来的不可知性,害怕我们的努力终将得不到公正的回报。但是正如我喜欢的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一篇小说,《南方高速》,在一场现实到无以复加,又奇幻到无以复加的大堵车后,科塔萨尔在最后写道:“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人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
封面新闻:在进入文学的世界过程中,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书是让你觉得给你带来启发比较多的?为什么?现在在读的书是什么?
焦典:非洲和马华文学,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偏爱的。非要说原因,也许是里面,那种作为“异类”和“少数”的东西。例如作家古尔纳《朝圣者之路》里的一个片段,达乌德和凯瑟琳在桥上漫步,两个肌肉男侮辱挑衅了他们。凯瑟琳按住达乌德的肩膀,对他说:“挺住,亲爱的。别变得愤愤不平、扭曲了你的心。那并不值得。”我有时甚至会觉得,凯瑟琳也按住了我的肩膀,在遭遇或者是回忆起一些同样不公的时刻。当我们身为某个地方或者人群中的“异类”或者“少数者”,就需要对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觉。但是这种警觉和抵抗不是某时某刻,而是时时刻刻,这是一种持续的压力。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种“异类”和“少数”或许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毕竟谁能保证永远站在大路中央?
封面新闻:几年前我采访你,谈到对文学写作未来的打算。你当时说,你希望一直写下去。几年过去了。你的想法有变化吗?
焦典:我可以很开心地说,没有变化。而如您看到的,我始终走在路上。
责任编辑:
网址: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作家?科班出身的焦典用热情将天赋与知识打通|当代书评·专访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9072
相关内容
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作家?科班出身的焦典用热情将天赋与知识打通|当代书评·专访作家毕飞宇:要想“手高”,必须首先“眼高”|当代书评·专访
邱天:芒果美术馆要引领年轻人的审美 | 专访
如何写作一篇书评
95后青年作家衡夏尔:写诗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当代书评·专访
6年书评作者,转型家庭教育父母心理陪跑,原因只有一个
“深圳文典”系列丛书推出青年作家武捷宇长篇小说《蕉鹿》
作家张楚出新作《云落》,用小说构建一个“县城宇宙” |当代书评
从这些访谈中,看到最前沿的思想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度合订本热卖中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出炉啦!

